夫妻离婚,房子归谁?若购房时父母有出资,房产又该如何分?针对此类审判实践疑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自2025年2月1日起施行。采访中,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发现:从不少案例来看,上海基层法院早已如此判决。对此,业内人士认为,这次只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统一和固定下来。
婚后一方把婚前房产
变更为另一方独有是全部赠与吗?
夫妻一方在婚内将其婚前购买的房屋产权变更为另一方独有,可以视作对另一方的全部赠与吗?松江法院就审理了一起这样的离婚案件。
离异的张先生在网络上认识了打算再婚的谢女士,两人结婚后,因为张先生体质原因,受孕困难,双方便做了试管婴儿。为了成功受孕,谢女士打了200多针保胎针,为此吃尽了苦头。张先生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于是为谢女士写下了《婚内协议》:“女方在做试管过程中非常艰辛且身体受损严重。双方约定不论成功与否,也不论男女双方哪方原因都将不离不弃白头偕老,如若因任何原因导致婚姻失败,男方须将名下房产及车辆赠与女方作为日后的生活补贴。特此协议。”尾部张先生签字。
谢女士怀孕八个月的时候,就各种软磨硬泡,要求张先生将其婚前购买的一套价值千万的房屋过户到她名下,张先生在咨询了不动产交易中心工作人员之后,答应了谢女士的要求,将其婚前房屋过户至谢女士名下。
然而,孩子出生后,仅过了一年多,谢女士就因生活琐事向张先生提出离婚。在离婚诉讼中谢女士称:张先生自愿写过《婚内协议》,房屋已经过户至女方一人名下,房屋已经完全属于谢女士的个人财产。
张先生则认为:自身出于回应原告请求以安抚对方情绪并维系双方感情的目的,才做出此过户登记行为,其认为房屋变更至谢女士名下系“配偶之间变更”,本意并非对原告的全部赠与,双方也未签订书面赠与合同,其绝对无完全赠与谢女士的意思。看在夫妻一场,张先生同意支付谢女士房屋价值10%的折价款。
松江法院审理后认为,首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婚内协议》以被告放弃巨大财产利益的形式限制被告的婚姻自由,违背了法律规定,且该协议的内容不符合法律所保护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度,故该协议无效。
其次,根据法院已查明的事实,该房屋权属进行转移登记时原被告仍系夫妻关系,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该房屋产权变更系双方基于约定或者基于赠与而进行,从夫妻之间更名的性质考虑,尽管目前房屋登记在原告一人名下,仍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最终,松江法院综合考量该房屋的出资贡献大小、权属、价格、银行贷款及还贷、居住使用情况、婚姻存续时间、对家庭的贡献以及公平合理等因素,判决房屋仍归被告所有,由被告向原告给付约40%的房屋折价款。
一审判决后,谢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经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父母出资购买房屋
离婚时如何分割?
民间将《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称为“新婚姻法”,其第八条就父母在子女婚后为其购房出资的认定做出规定。该规定施行后,对于法院处理离婚纠纷中房屋分割问题将有较大变化。
“简言之,就是一方父母全额出资情况下,无论赠与合同是否明确约定,房屋原则上归属于全额出资一方子女。一方或双方父母部分出资情况下,如不存在明确约定,则由法院以出资来源及比例为基础综合判断房屋归属于其中一方子女。”闵行法院段文澜法官普法道,“关于补偿,一方父母全额出资情况下,由法院酌情考量获得房屋一方是否需要补偿以及补偿的金额(并非一定需要进行补偿)。一方或双方父母部分出资情况下,获得房屋一方须对另一方进行合理补偿(需要补偿)。”
浦东法院就有这样一个案子:原告赵先生与被告陈女士离婚诉讼时并未分割双方间的财产权益。离婚后,赵先生向浦东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将被告在原、被告婚姻期间购买的一套长宁区的房屋判决为按份共有。该不动产的出售总价为216万(到手价),原告要求其中1.83%归其所有,理由是:购房款项中有部分属于原、被告所有。
浦东法院审理后认为,如果系争房屋的购买为被告父母全额出资,则系争房屋为被告的个人财产,否则,为原、被告夫妻共同财产。现在法院认定原、被告共同出资4.16万元的情形下,原告主张其占系争房屋的产权份额为1.483%,法院予以支持。
由此,法院判决:系争房屋归被告陈女士所有,被告陈女士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向原告赵先生支付房屋折价款34104.44元。
一方抢夺未成年子女
另一方可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
值得关注的是,《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的新规包括:一方或其他近亲属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另一方可以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记者发现,上海基层法院此前也有类似案件,今后维权一方可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
静安法院就有这样一个案例:卢女士与王先生结婚8年,育有一女小王。婚姻中,夫妻双方因性格不合,经常为生活琐事发生激烈争吵。
2022年1月,卢女士发现家里门锁被王先生调换,于是在未告知王先生的情况下,将6岁的小王带回卢女士老家,并擅自将小王学籍转至老家,王先生多方寻找无法得知小王下落。
同年9月,卢女士将小王带回上海,双方在小王新学校门口发生争执,在警方调解下,双方就探望事宜达成初步口头协议,但未能实际履行。
2023年1月,王先生带四五人,趁卢女士父亲带小王散步,强行围堵卢女士父亲并抢走小王,之后将小王藏匿于外地。卢女士遂向静安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女儿随自己共同生活,王先生表示同意离婚,但同样要求抚养女儿,双方在女儿的抚养权归属上发生分歧。
静安法院认为,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将对孩子的成长和身心发育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尤其对于低龄儿童来讲,较长时间的分离将严重损害亲子关系。在处理离婚纠纷之前,法官对卢女士和王先生抢夺、藏匿子女的行为进行了严肃批评和法庭教育,并制发了家庭教育令,同时责令王先生限期将小王带回上海。
2023年5月,青少年社工对小王开展了心理疏导工作,以减轻父母不当行为对小王造成的不良影响。卢女士和王先生在家事调解员的调解下,就离婚诉讼期间小王的抚养和探望达成一致,约定在此期间小王跟随母亲生活,父亲定期探望。双方均恪守履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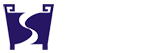



 客服1
客服1